高考分数线调整对教育公平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维度性,不同阶层学子在升学机会上的差异既受到政策设计的直接影响,也与家庭资本、教育资源分配等结构性因素密切相关。以下从多个层面分析其影响机制:
一、分数线调整的直接机会扩展效应
1. 本科线下降与中等生受益
2024年多省本科录取线普遍下降(如河南理科二本线降至408分,新疆理科一本线仅390分),2025年预计部分省份本科线可能进一步降低至400分左右。这种调整短期内为成绩处于中下游的学生(尤其是农村和低收入家庭子女)提供了更多进入本科院校的机会,缓解了“唯分数论”下的升学焦虑。
2. 批次合并与选择灵活性提升
2025年新高考政策取消传统一本、二本划分,改为提前批、本科批和专科批,弱化高校等级标签。此举理论上扩大了中下层学生冲刺优质院校的可能性,例如二本线学生可竞争原一本院校冷门专业。填报复杂度上升可能加剧信息不对称,弱势家庭因缺乏专业指导更易陷入“伪冷门”陷阱。
二、家庭资本的隐形调节作用
1. 信息与策略博弈中的阶层分化
新高考模式下,选科组合(如“3+1+2”)和赋分机制(如化学卷面85分可能被赋分至70分)要求学生具备前瞻性规划能力。优势阶层家庭可通过购买“选科大数据库服务”、职业测评工具等,帮助子女优化科目组合,而底层家庭更多依赖有限信息被动选择。例如,辽宁物理类本科线比历史类低32分,但选物理需匹配未来理工科专业的高要求,弱势家庭子女可能因误判而错失机会。
2. 升学服务与综合素质竞争
高考改革强调综合评价(如强基计划、专项招生),但农村学生参与竞赛、科研项目的比例显著低于城市学生。例如,2025年强基计划要求竞赛经历,而底层家庭难以负担相关培训费用。专项计划(如国家专项)虽为农村生降分,但部分偏远地区学生因信息闭塞未能有效申请。
3. 文化资本与志愿填报风险
平行志愿模式下,“冲稳保”策略依赖对历年录取数据的精准分析。高学历父母更擅长利用高校排名、专业就业率等数据辅助决策,而低学历家庭可能因认知局限选择保守策略,导致分数利用率偏低。
三、结构性矛盾与政策局限性
1. 地域差异的制度化不公平
直辖市(如北京、上海)的985高校外地招生率显著高于其他省份(北京考生进入武汉大学的概率是河北考生的6倍),这种地域保护主义使优质教育资源向经济发达地区倾斜,抵消了分数线普降的公平效应。例如,上海本科线仅403分,但其基础教育投入和升学服务远超中西部省份。
2. 教育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

农村地区学校生涯教育普遍滞后,弱势家庭难以通过学校指导弥补信息劣势。研究显示,学校生涯教育虽能促进家长参与,但对弱势阶层的补偿效应尚未显现,家庭资本仍是升学准备的主导因素。普高率提升至75%可能加剧高考内卷,底层学生进入普通高中后仍面临课程适应困难。
3. 政策滞后与执行偏差
新高考赋分制、选科指引等改革旨在遏制功利选科,但执行中仍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例如,部分中学为提升升学率,强制学生选择易得高分的科目,而非基于兴趣或职业规划。
四、优化路径与未来展望
1. 强化信息透明与公共服务
建立全国统一的志愿填报信息平台,提供免费选科模拟工具和职业倾向测试,减少家庭资本的信息垄断。例如,浙江“三位一体”招生模式通过综合评价降低分数权重,值得推广。
2. 深化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加大农村地区生涯教育投入,通过“家校联动”培训提升弱势家庭参与度。研究证明,学校资本对父母教育参与有显著促进作用,但需长期投入才能显现补偿效应。
3. 改革招生名额分配机制
探索按适龄人口比例分配高校招生名额,逐步消除地域保护主义。例如,将京津沪部分高校招生名额向人口大省倾斜,缓解河南、山东等地的录取率洼地问题。
4. 完善多元评价体系
拓宽专项计划覆盖范围,将更多城市贫困家庭纳入政策惠及对象。加强综合素质评价的规范性监管,防止隐性歧视。
高考分数线调整仅是教育公平的“表面工程”,其实际效果受制于深层的结构性不平等。唯有通过政策优化、资源再分配和家庭-学校-社会的协同干预,才能为不同阶层学子构建真正公平的升学通道。正如布迪厄所言,教育系统的“文化再生产”功能若未被打破,弱势群体仍将困于代际传递的桎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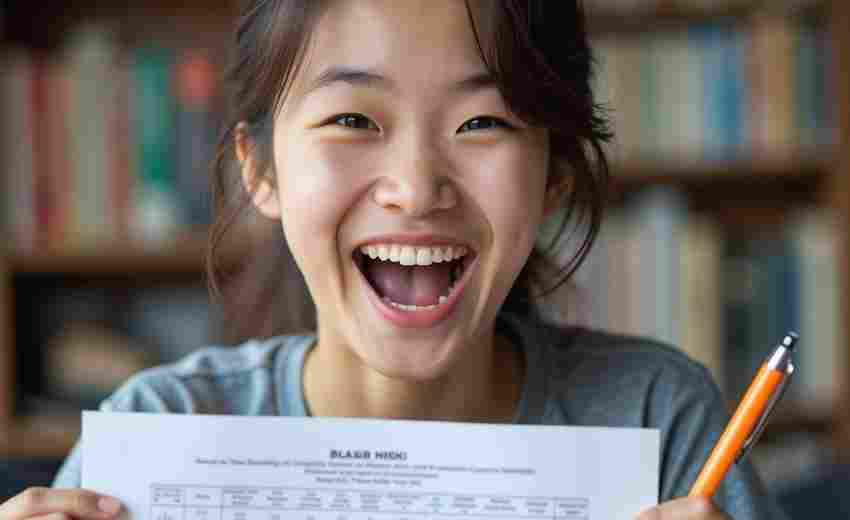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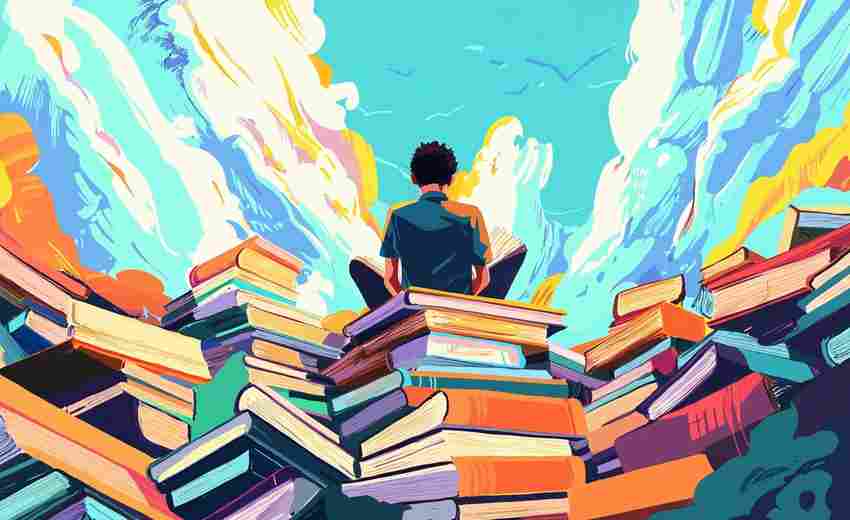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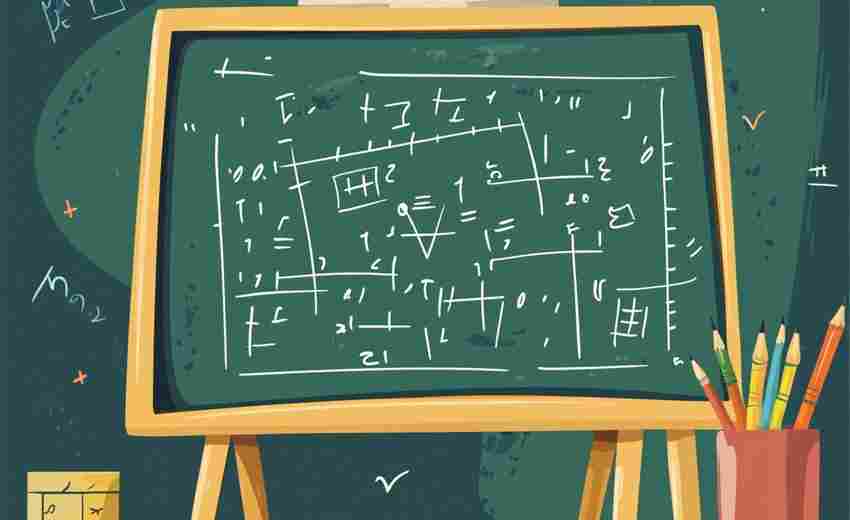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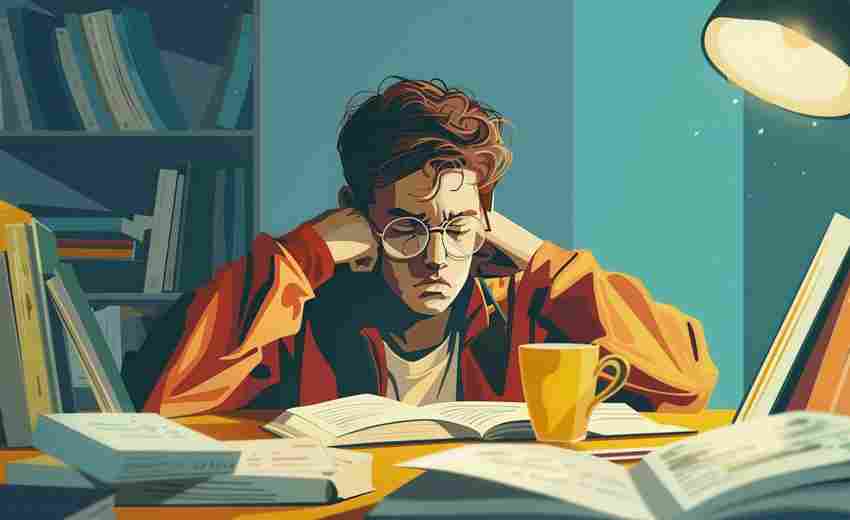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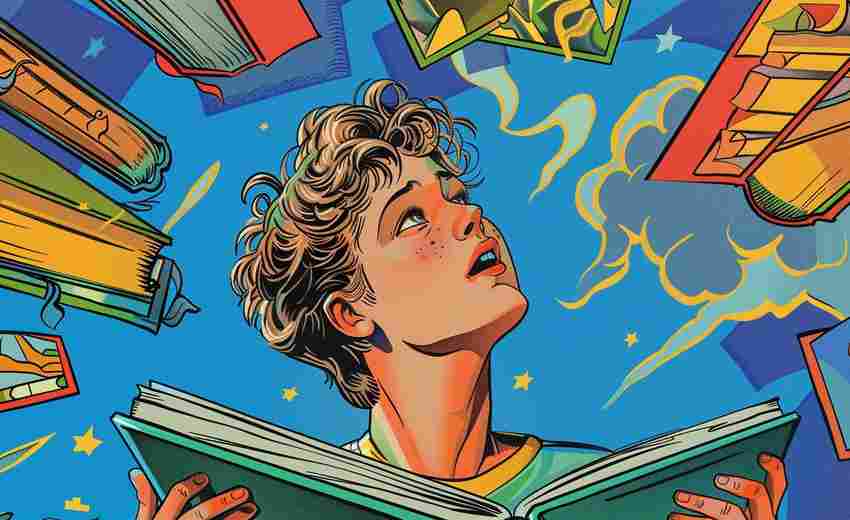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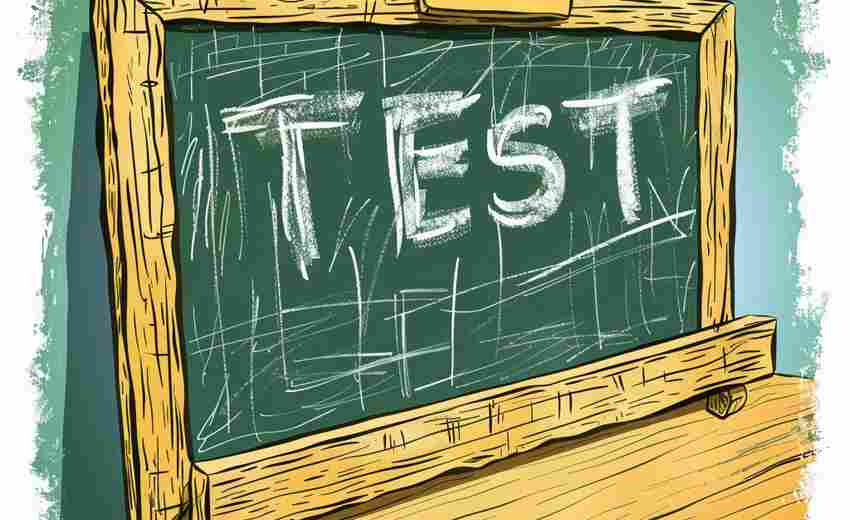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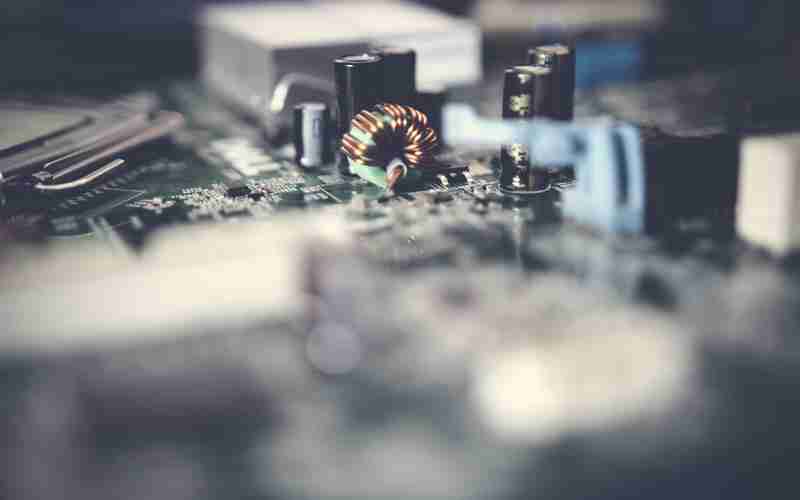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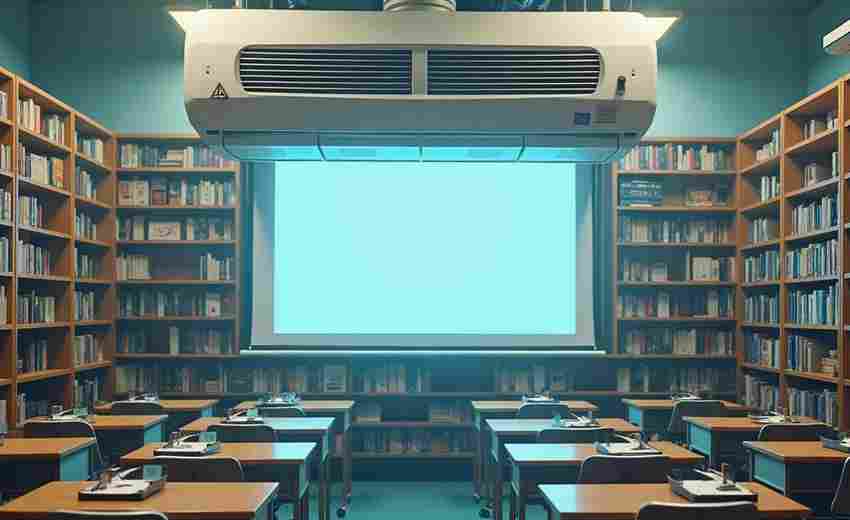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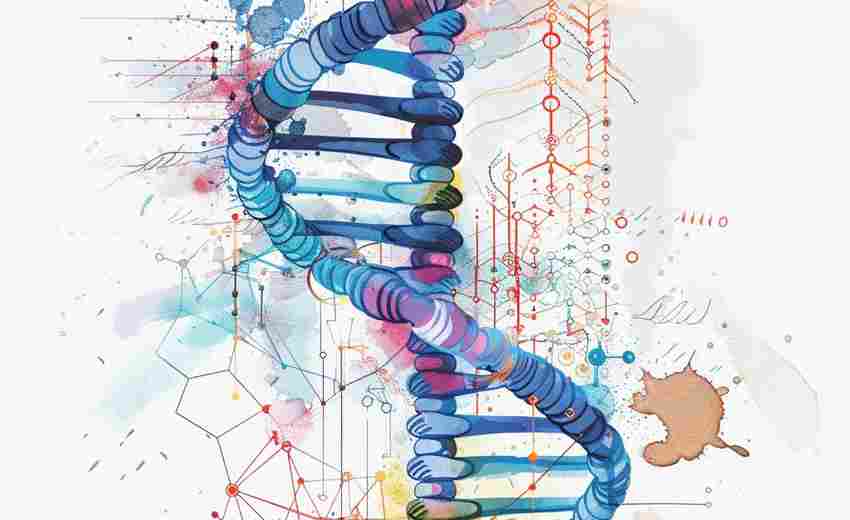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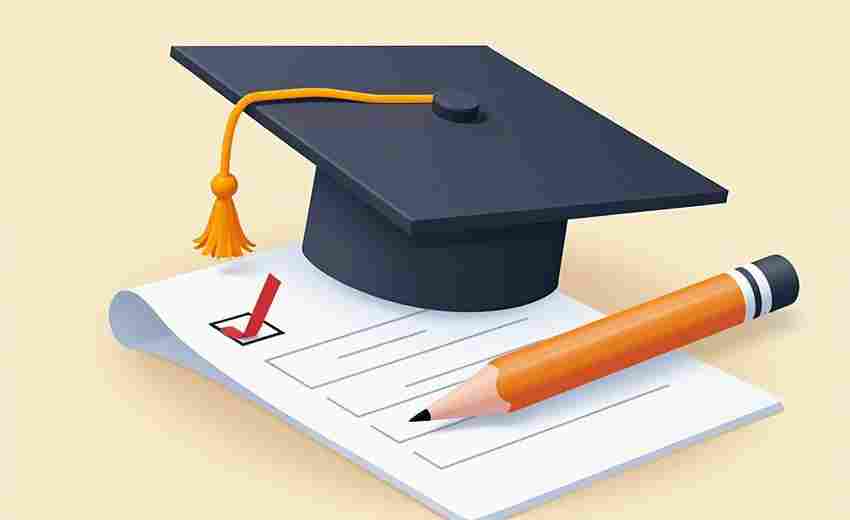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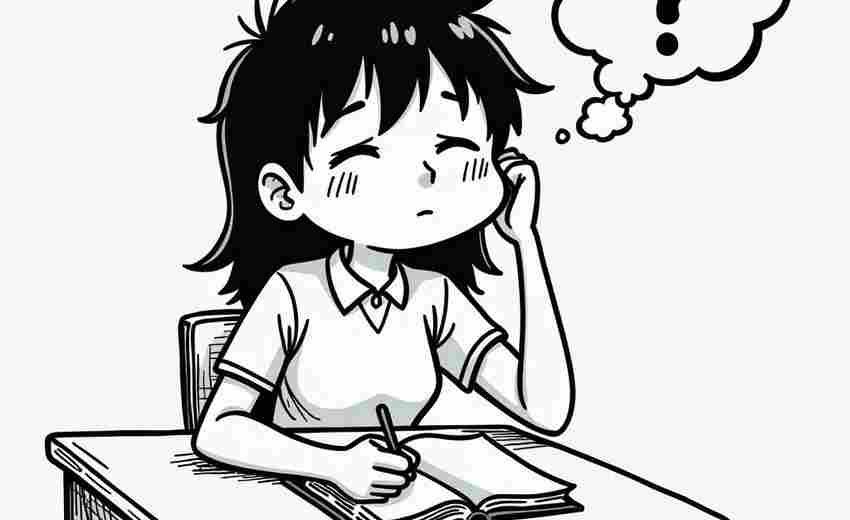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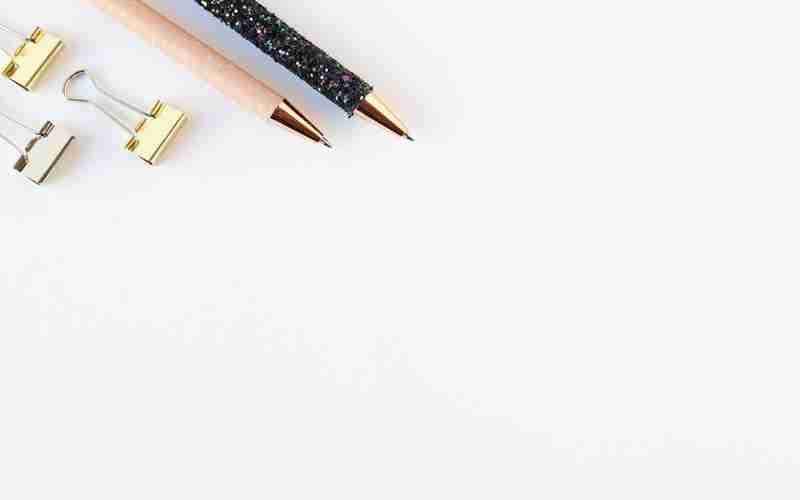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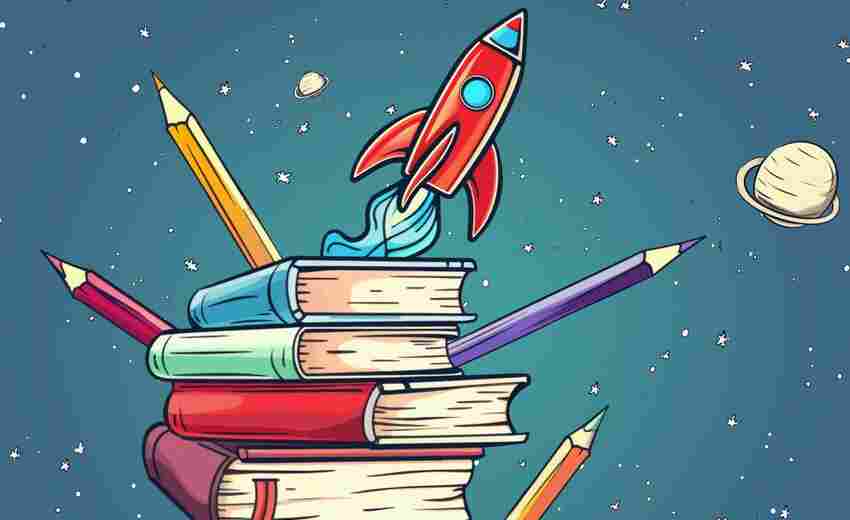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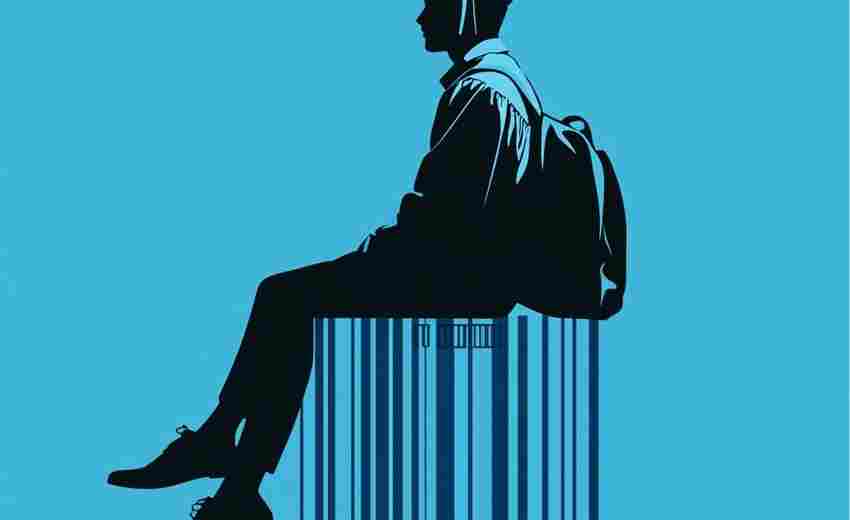





推荐文章
高考英语听说能力提升:日常训练与考场应对
2025-04-06如何利用高考成绩制定长期职业规划
2025-02-28电气工程专业的技术趋势有哪些
2025-02-17高考志愿填报中的服从调剂是什么意思
2025-01-18动漫专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如何
2025-01-29如何评估自己是否适合继续深造
2025-01-18春季高考是否有自主招生的机会
2025-02-20生物科技专业的热门方向有哪些
2024-12-13高考志愿卡填写的法律责任是什么
2025-02-21体育教育专业的职业发展方向
2025-0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