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政策调整作为教育领域的重要改革举措,其背后涉及多维度的教育管理学因素。结合当前政策动向及学术研究,以下从教育管理学的核心理论、实践挑战及优化策略三个层面进行解析:
一、教育管理学理论视角下的政策调整动因
1. 系统理论与整体性治理
高考改革需协调教育系统内外的多元利益主体(如学生、学校、、社会),通过“3+1+2”选科模式和综合素质评价,打破传统文理分科的割裂状态,推动教育系统的整体性优化。例如,等级赋分制和院校专业组模式旨在通过资源再分配和流程重组,减少因学科难度差异导致的不公平问题。
2. 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教育管理学强调公共政策的公平性导向。取消一本、二本、三本批次划分,改为本科提前批、普通批和专科批,旨在弱化高校等级标签,促进生源流动和资源均衡。禁止公立学校招收复读生的政策,则是通过限制资源倾斜来维护应届生的公平竞争环境。
3. 权变理论与动态适应性
高考政策需回应社会变迁需求。例如,物理选科人数“断崖式下滑”暴露了等级赋分的局限性,促使“3+1+2”模式中固定物理或历史为必选科目,体现了政策对学科结构失衡的动态调整。
二、政策实施中的管理挑战与矛盾
1. 利益相关者的多元诉求冲突
2. 评价体系改革的技术困境
3. 政策执行中的路径依赖
传统“唯分数论”思维惯性导致应试负担加重,部分学校仍以分数排名为导向,与新高考倡导的“考能力”目标形成张力。
三、教育管理学视角下的优化策略
1. 构建协同治理机制
2. 完善动态监测与反馈体系
3. 强化利益相关者参与
4. 推动教育组织变革
四、未来趋势与管理启示
1. 技术赋能管理创新
人工智能与区块链技术可应用于考试安全(如防作弊)、成绩追溯(如等级赋分算法优化)等领域,提升政策执行的科学性。
2. 国际化与本土化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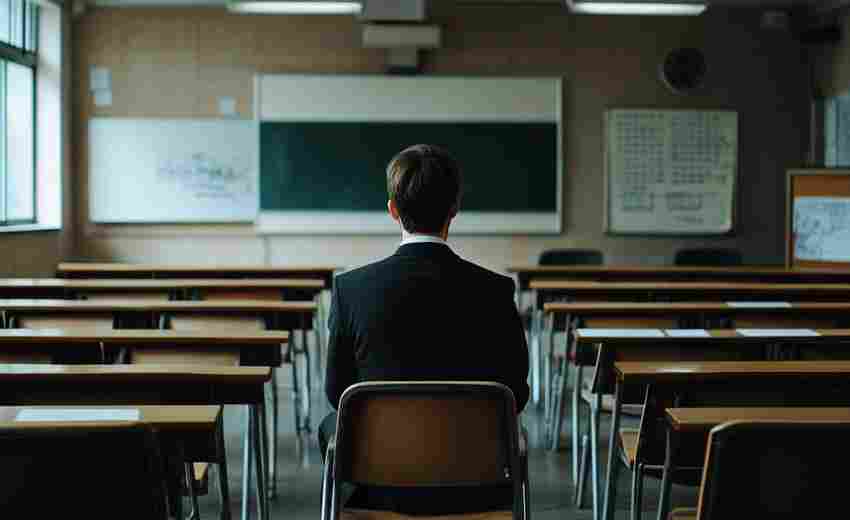
借鉴芬兰大学入学考试等级评定等国际经验,结合国情探索综合评价模式,避免简单移植导致的“水土不服”。
3. 终身学习导向
高考改革需与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体系衔接,例如通过专科批次优化拓宽人才成长通道。
高考政策调整是教育管理学理论在实践中的复杂映射,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平衡公平、效率与质量。未来改革需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动态适应和多元共治,推动教育治理从“管理”向“治理”转型,最终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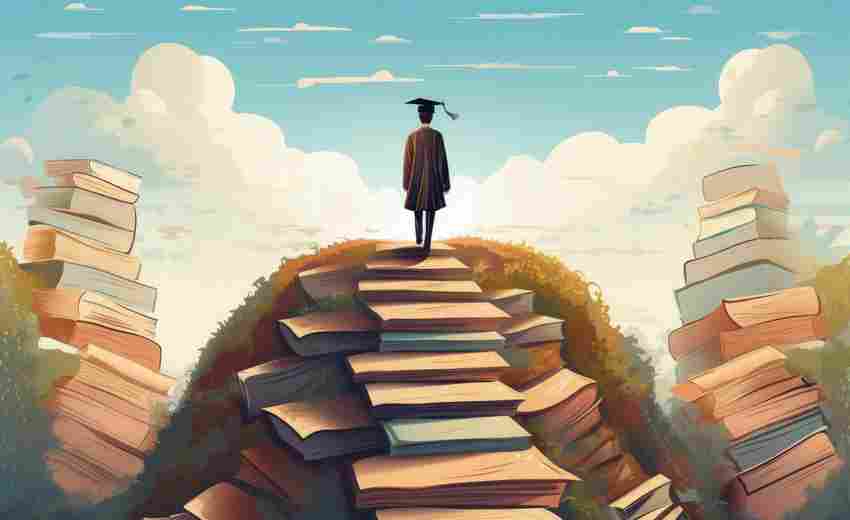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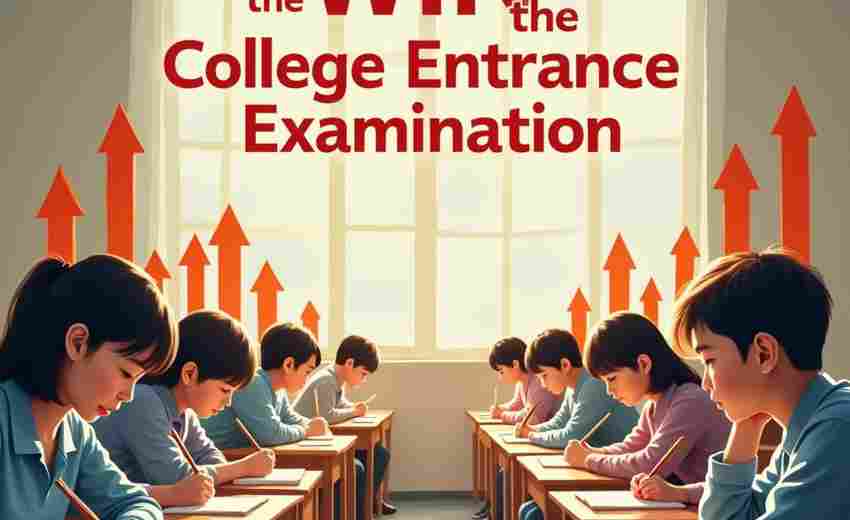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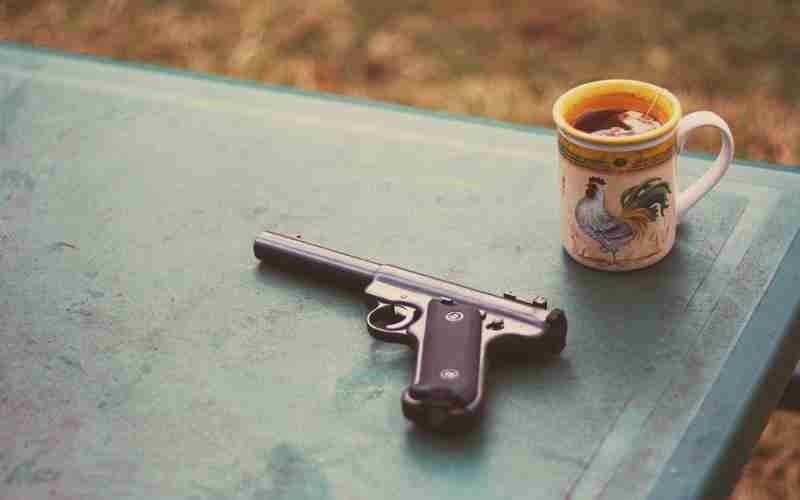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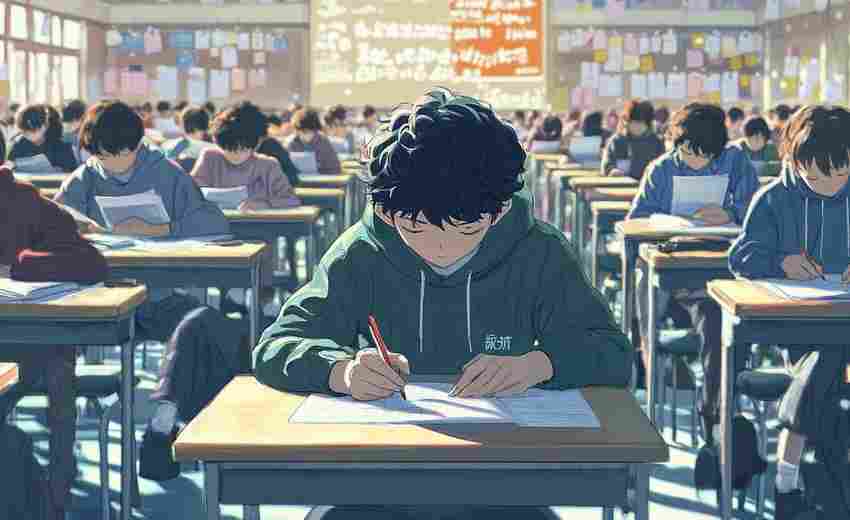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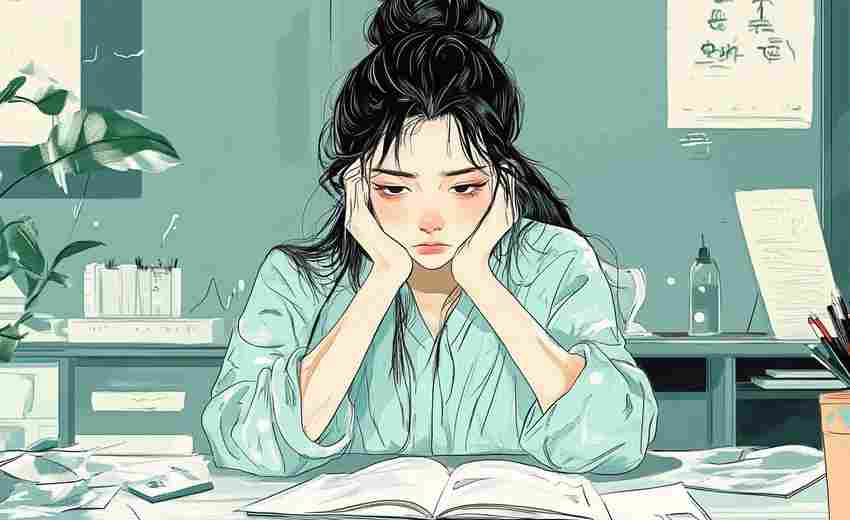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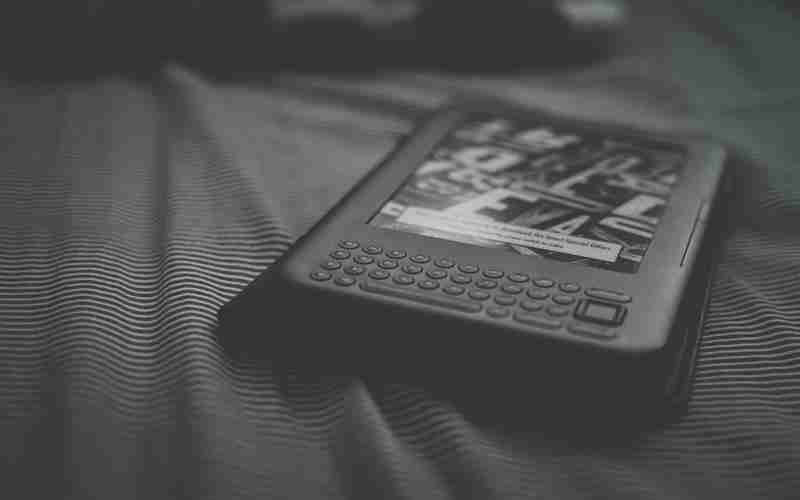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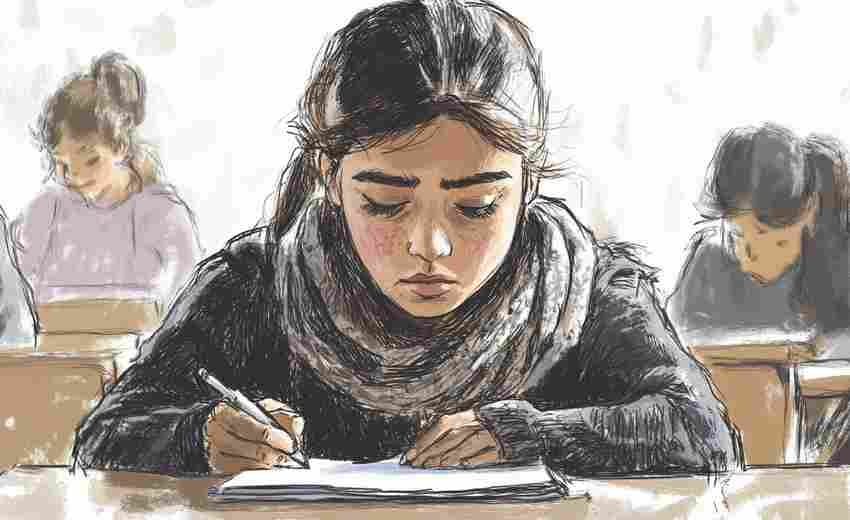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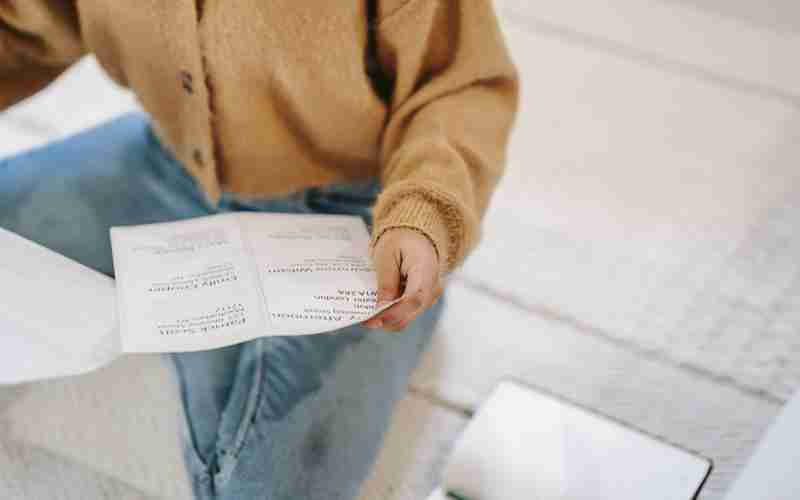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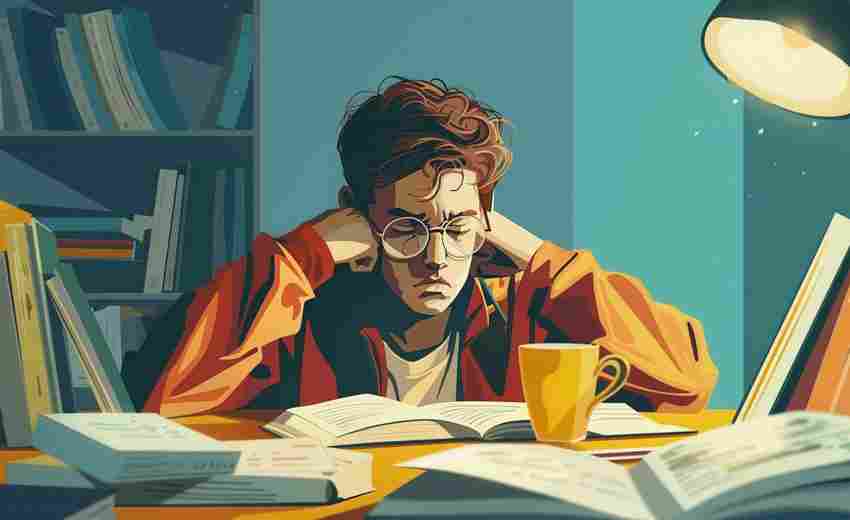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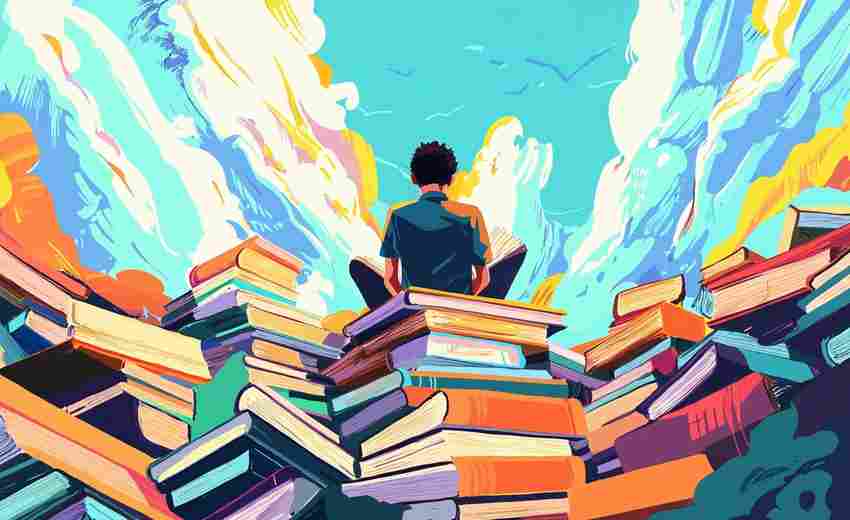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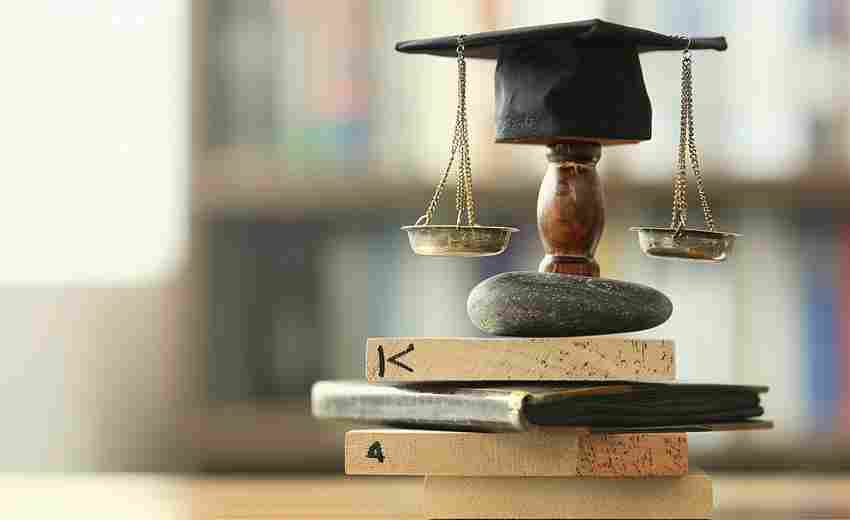
推荐文章
高考经济类考题如何区分资产管理VS财富管理
2025-03-18考军校的复习资料推荐
2025-01-02高考报名号的查找方式有哪些
2025-02-10调剂成功后能否更改专业
2025-01-09传媒专业的就业机会如何
2025-01-19高分数线对考研的影响有哪些
2024-12-13临床医学专业高考录取分数线及趋势分析
2025-03-23风险管理的主要步骤是什么
2024-11-27文化自信的满分作文需要哪些核心要素
2025-03-12专业课程中的实践环节重要吗
2025-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