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参与率与人口红利的辩证关系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命题。结合高考考点的延伸需求,可从以下维度展开分析:
一、概念内涵与基础关系
1. 人口红利的本质
人口红利是指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占比较高、抚养比(少儿+老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较低的阶段,形成高储蓄率、高投资率的经济增长优势。其核心是人口年龄结构对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2. 劳动力参与率的定义
劳动力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就业者+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反映劳动力资源实际投入生产的程度。例如,2020年中国劳动参与率约为68%,显著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3. 二者的直接关联
在人口红利期,高劳动参与率是释放人口红利的核心路径。例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措施,将劳动参与率提升至70%以上,充分挖掘劳动力规模优势。
二、动态演变:从数量红利到质量红利
1. 传统数量型红利的依赖

劳动力规模驱动:1978-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从5.6亿增至10亿,叠加高劳动参与率(65%以上),形成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经济效应: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制造业)的扩张依赖高劳动参与率,推动出口和资本积累。2. 转型期的矛盾与挑战
劳动力数量萎缩:2010年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规模双下降,2022年减少至9.7亿人,传统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参与率下降的制约:老龄化加剧(2025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14.9%)导致劳动参与率下行,如青年教育周期延长、女性生育成本增加等。3. 质量型红利的重构
人力资本替代:通过教育投入提升劳动生产率(如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7.8%),以“人才红利”弥补数量缺口。配置效率优化:劳动力从农业向服务业、传统制造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辩证关系的核心逻辑
1. 互补性
短期互补:在人口红利窗口期,高劳动参与率通过扩大就业规模直接释放人口红利。例如,农民工进城务工推动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升至2020年的64.7%。长期协同:劳动力参与率的结构优化(如延长退休年龄、女性就业支持)可延缓人口红利衰减。2. 矛盾性
数量与质量的冲突:过度依赖劳动力规模可能导致低端产业锁定,抑制技术创新;而产业升级可能短期内减少就业岗位,降低参与率。老龄化与参与率的博弈:老年人口增加可能降低整体劳动参与率,但开发“银发人力资源”(如延迟退休、老年再就业)可形成新红利。四、政策启示与高考应用
1. 政策方向
提升劳动参与率:完善托育服务减轻女性负担,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对接。深化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基础教育普及和技能培训,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优化人口结构:通过生育政策调整、户籍制度改革平衡区域劳动力供需。2. 高考考点链接
地理:结合人口迁移(农民工进城)、城市化(劳动力空间再配置)分析区域经济差异。政治:从“社会保障制度”“新发展理念”角度论述劳动力参与率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历史:对比改革开放初期与当前人口政策的演变,理解经济转型的历史逻辑。劳动力参与率与人口红利的辩证关系体现了经济发展中“量”与“质”的动态平衡。当前中国正经历从“规模驱动”向“效率驱动”的转型,需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重构新型人口红利。这一过程既是挑战,也为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提供了历史机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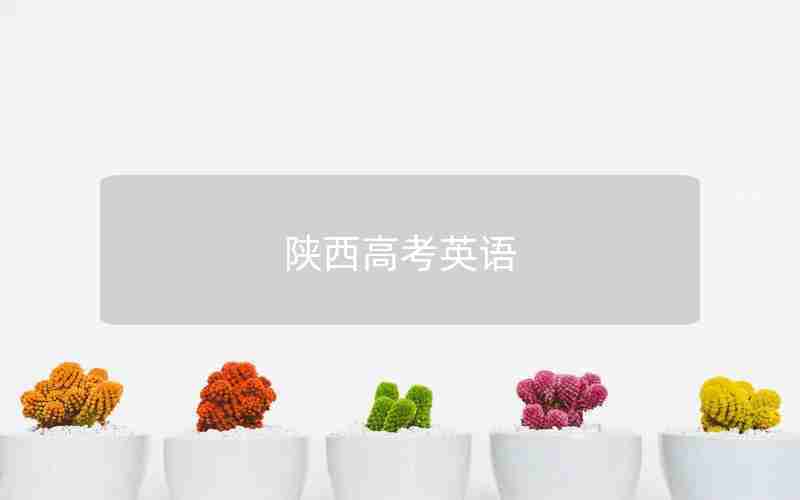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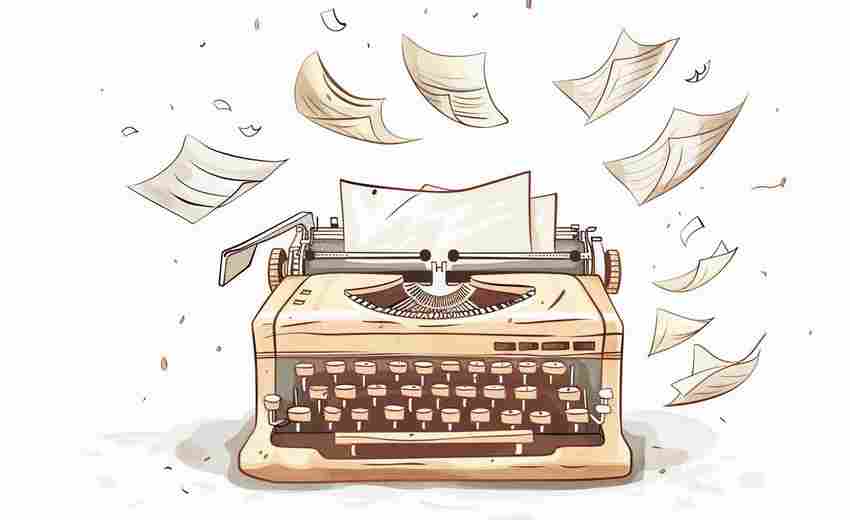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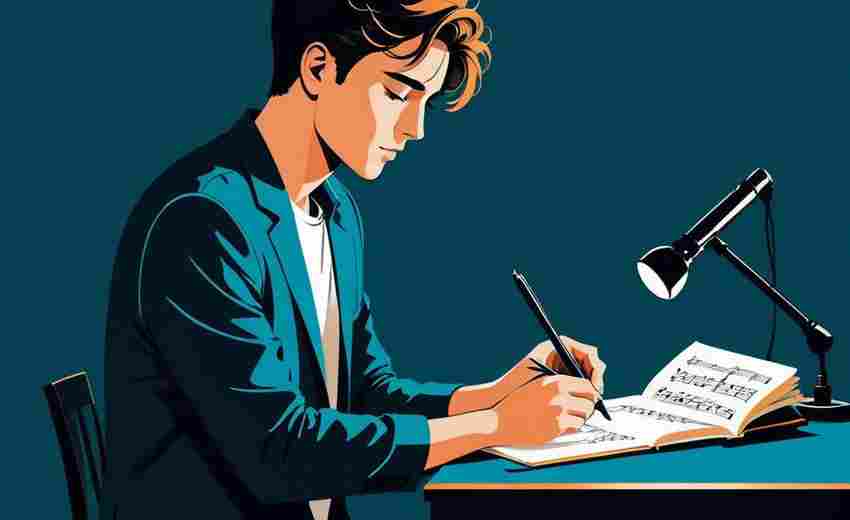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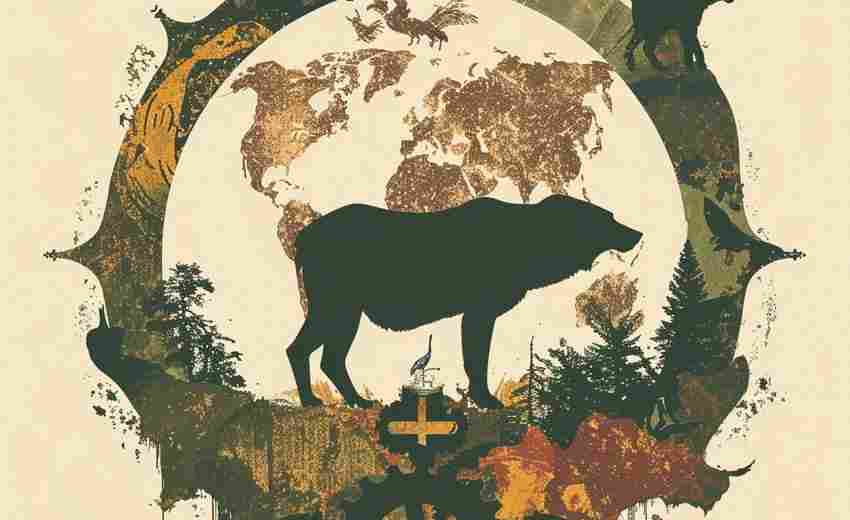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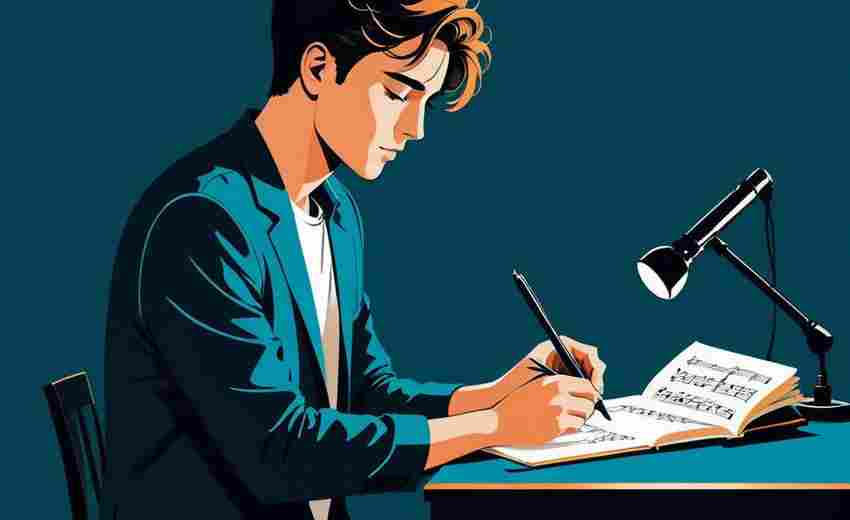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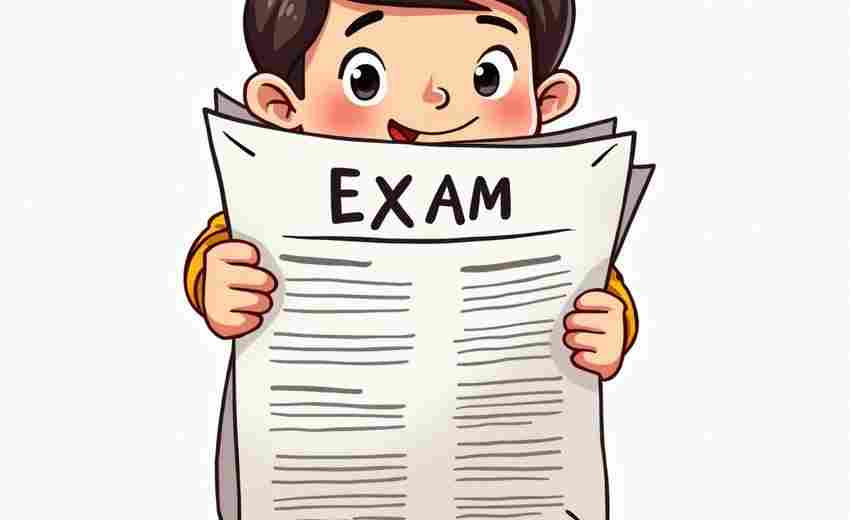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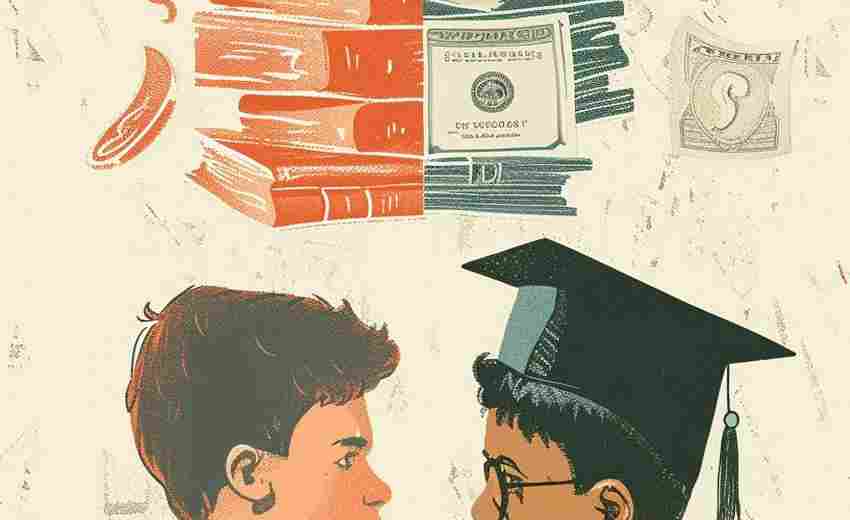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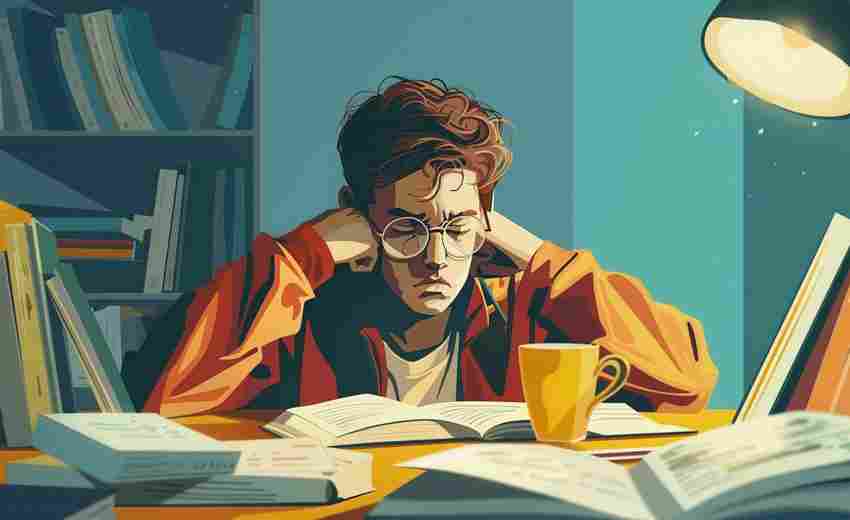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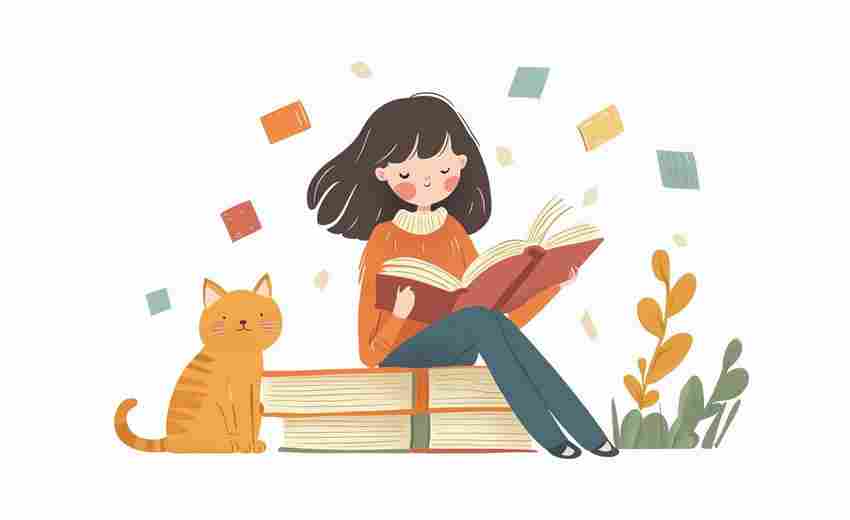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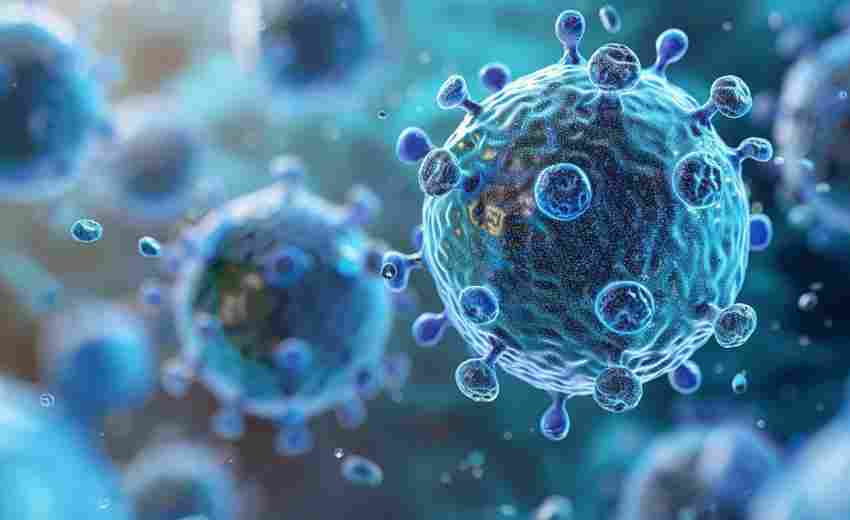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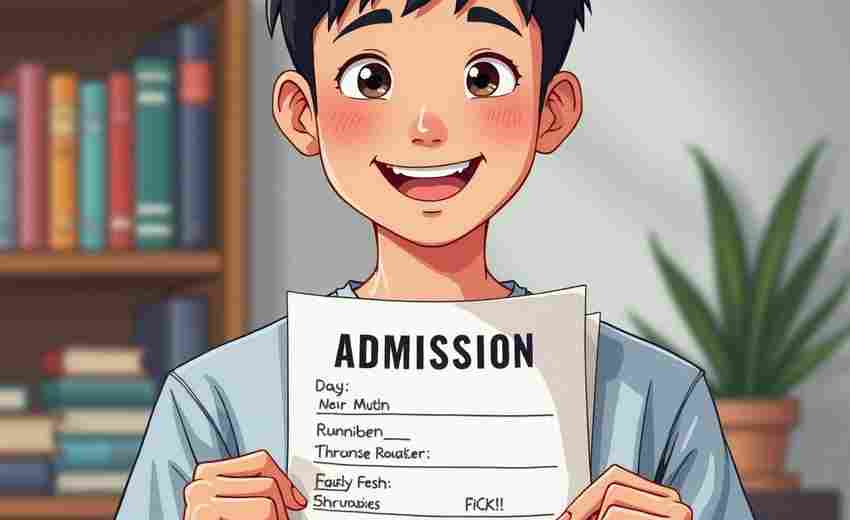
推荐文章
数据分析在市场营销中的作用是什么
2025-01-20如何分析分数线对未来学习的影响
2025-03-04高考志愿调剂的成功率高吗
2025-02-03高考前选择专业的重要性是什么
2024-11-27艺术设计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2024-11-17在反恐中的具体职责是什么
2025-02-27高考志愿填报中第一志愿为何影响录取成功率
2025-04-12如何提升高考语文阅读理解能力
2024-12-21高校专项计划与普通批次录取冲突如何解决
2025-04-11公共管理专业的就业领域是什么
2025-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