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因素在高考专业选择和职业规划中扮演着多维度、深层次的角色,既体现为物质资源的支持,也渗透于价值观传承与职业认知的塑造。以下从五个核心维度展开探讨:
一、职业传承与经济条件的显性影响
1. 职业世家的隐性引导
家庭成员职业背景会通过日常互动形成职业认知框架。例如,父母从事外向型经济行业,其社交经验与经商渠道可能培养孩子对国际贸易或管理类专业的兴趣。研究显示,家庭中超过三代从事同一职业的情况,子女选择相关专业的概率显著提高。
2. 经济资本对专业选择的制约性
家庭经济状况直接影响教育投入方向:
二、文化资本与价值观的深层渗透
1. 教育理念的传递
父母受教育程度与职业态度直接影响子女规划意识。高学历父母更注重生涯规划的系统性,平均会提前2-3年引导子女进行职业测评(如MBTI)和行业调研。而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往往将专业选择简化为“就业导向”,忽视兴趣匹配。
2. 价值观的隐形塑造
家庭强调的价值观(如责任感、创新意识)会内化为职业。例如,父母从事公共服务职业的家庭,子女选择社会工作、教育类专业的比例比其他家庭高27%。这种影响甚至延伸到职场表现,如医生家庭子女在医学专业学习中表现出更强的抗压能力。
三、资源支持与决策参与的双重作用
1. 信息资源的差异化获取
优势家庭通过社会网络提供行业动态、实习机会等“软资源”。例如,金融从业者家庭可为子女安排投行实习,而普通家庭多依赖学校公开信息,易产生信息滞后。调查显示,重点大学经济类专业中,家庭有金融从业背景的学生占比达42%。
2. 决策权的博弈与平衡
家长参与呈现两种极端:
四、社会资本对职业发展的持续效应
1. 就业机会的阶层再生产
家庭社会关系直接影响职业起点。例如,父母为公务员的毕业生进入体制内的概率是普通家庭的3.2倍。这种现象在人文社科专业尤为显著,因其更依赖人际资源,而理工科专业通过技术能力突破家庭背景限制的可能性更高。
2. 职场适应性的代际传递
家庭职业经验能帮助子女规避职业陷阱。如经商家庭子女在市场营销专业学习中,对客户需求的敏感度比同龄人高19%。这种经验传承使他们在校招面试中更擅长展示家庭背景的积极影响(如稳定性、沟通能力)。
五、突破局限的科学路径
对于资源有限的家庭,可通过以下策略实现突围:

家庭因素既是职业规划的“启动器”,也可能成为“限制器”。关键在于将家庭影响转化为个性化发展的助力,例如通过家庭职业图谱分析(如图3所示),系统识别优势与盲区,最终在代际传承与个体自主性之间找到平衡点。教育部门需加强职业规划课程普及,特别是向县域中学倾斜资源,以缓解家庭资本差异导致的规划能力鸿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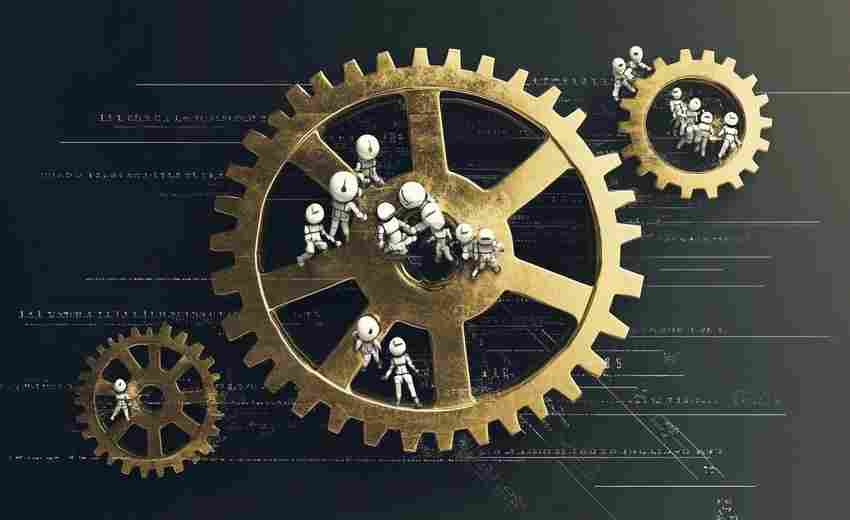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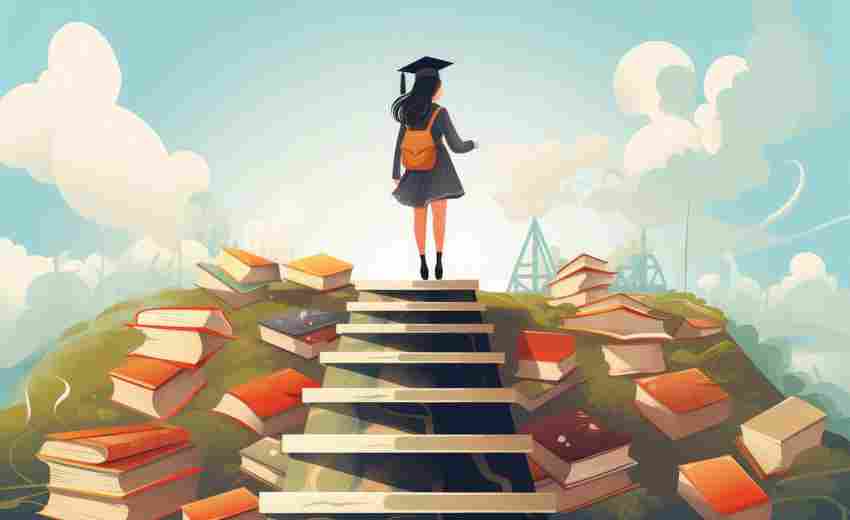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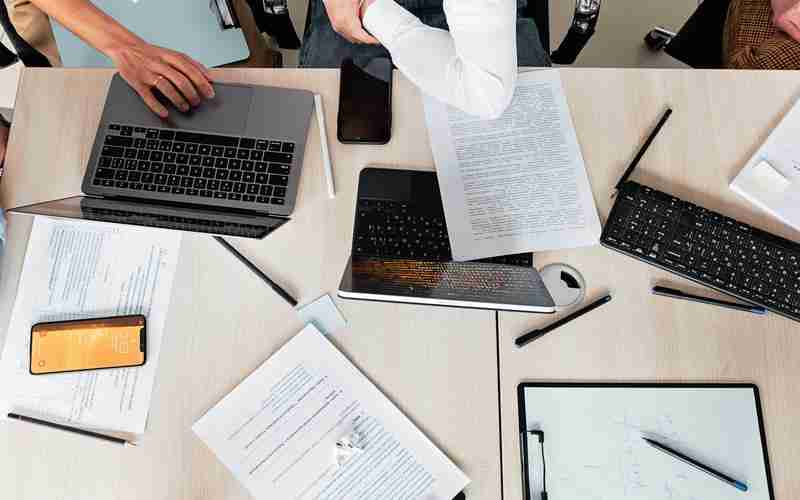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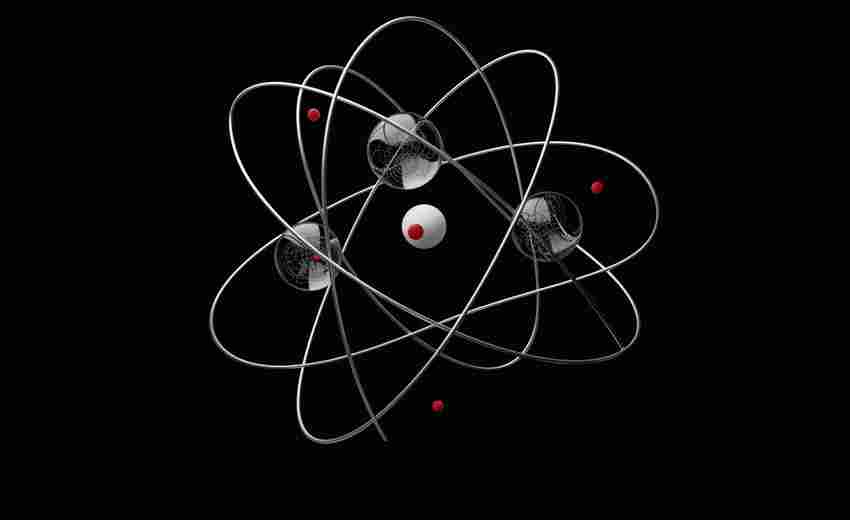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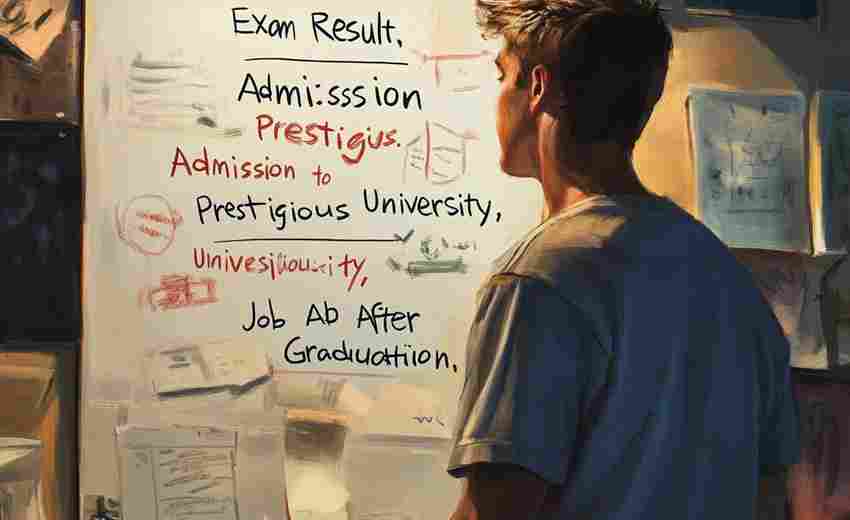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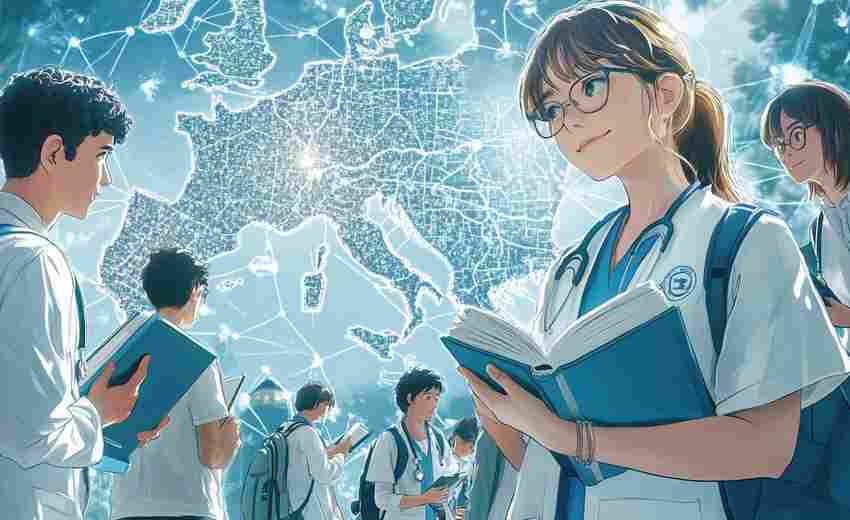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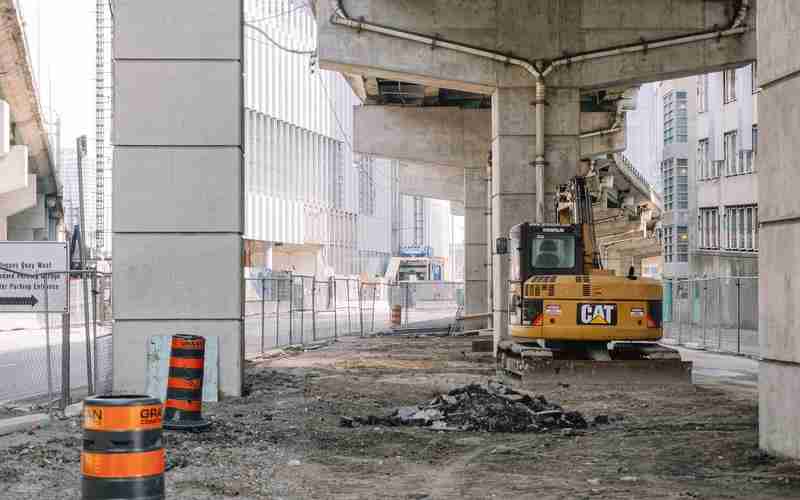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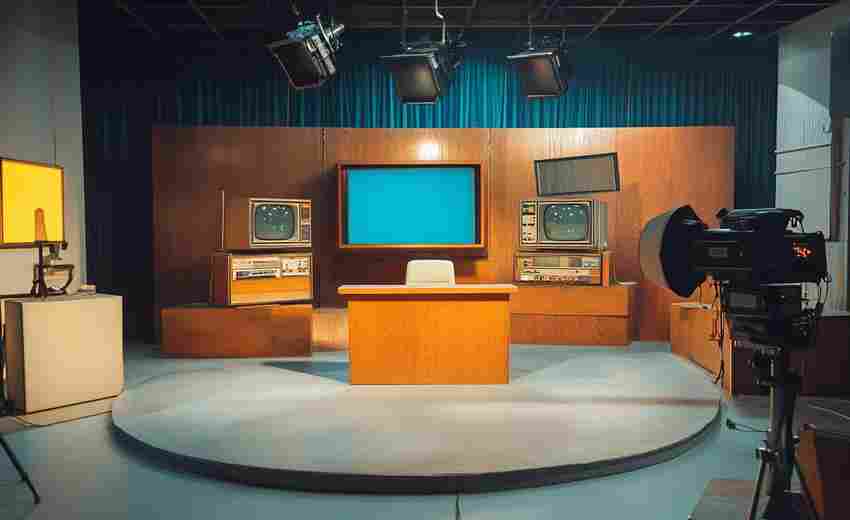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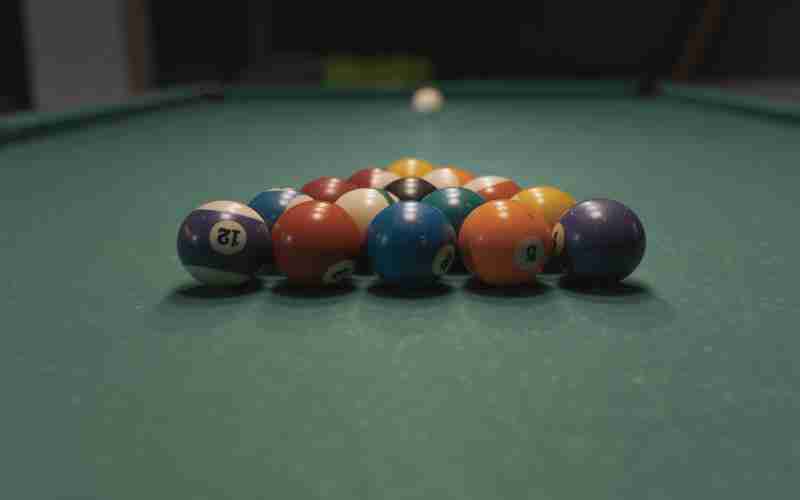












推荐文章
云南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学习内容如何
2025-01-03电子商务专业的就业机会如何
2025-01-24如何根据兴趣选择专业
2025-03-05神经科学的研究热点是什么
2024-12-22不同类型高校的调剂政策有何不同
2024-11-04统计学与数据分析的联系是什么
2024-12-17现代物理学的研究热点是什么
2025-01-28选择工科专业有哪些未来发展方向
2024-11-25口语高考-高考英语口语通过率高吗
2024-01-10音乐表演专业需要哪些素养
2024-11-09